《普陀山佛教史》序 一
2024-08-27
李利安教授
会闲法师和景天星博士合著的《普陀山佛教史》即将出版。感谢两位作者的抬举和信任,我得以有机会在这里表达随喜赞叹之情,并就相关话题谈一些自己的想法。
人类有四大宗教文化区,即印度教文化区、基督教文化区、伊斯兰教文化区和中华宗教文化区。从民众神灵信仰的对象来看,如果说,前三个宗教文化区最流行的神灵分别是梵天(或三大主神)、上帝、真主的话,那么中华宗教文化区最流行的神灵应该是观音菩萨。尽管四大宗教文化区的板块结构在全球化时代开始松动,不同宗教之间多元并存的空间格局正在试图突破原有的宗教文化区界限,但从中华宗教文化区乃至整个东亚宗教文化区来看,观音信仰的普及程度,特别是其文化底蕴及其对文学、艺术、民俗和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影响,在东亚神灵信仰的领域内可能依然无出其右者。这一宗教文化现象的形成,经历了多个令人惊叹的历史变迁,仅举四例如下。
两晋南北朝时期,观音作为威力无边、普济一切的救度之神,迅速从圣人崇拜、神仙崇拜、祖先崇拜、上天崇拜以及杂乱无章的自然神和鬼神崇拜现象中脱颖而出,以平等、威猛、慈悲、智慧、亲和的鲜明形象,一扫中国本土崇拜存在的功能狭窄、理论单薄、方式模糊等弊端,成为中华大地上最流行的一种保佑神。从此,威力无边、救苦救难的菩萨形象深入人心,对中国宗教神灵信仰体系形成巨大的冲击和补充,中国神灵信仰史由此步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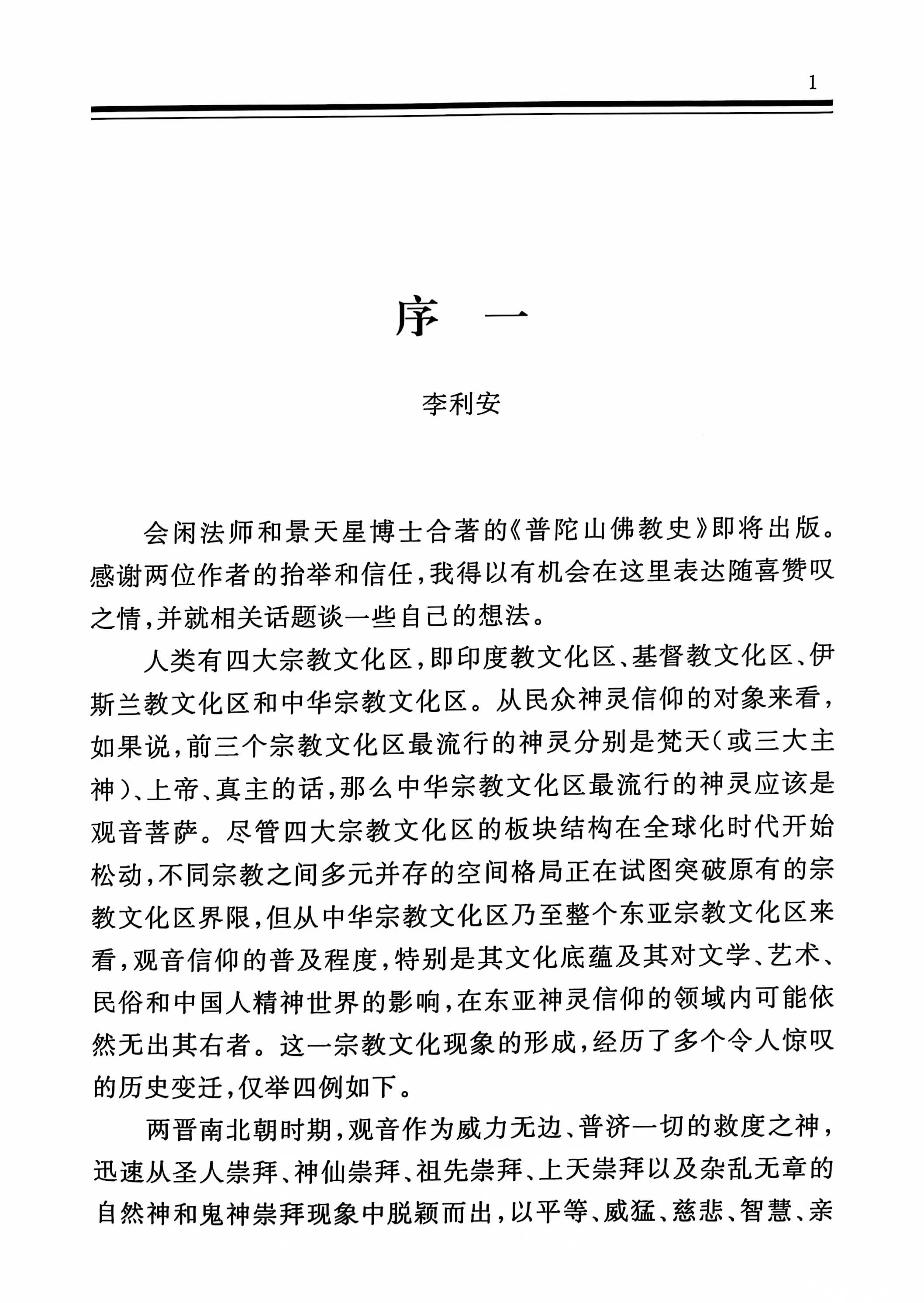
隋唐之际,观音信仰从单一的神力保佑信仰迅速拓展到智慧觉悟、净土接引、咒语加持、福德积累、指点迷津等多种信仰形态,而且都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并开始与当时处于鼎盛状态的佛教理论相呼应,与其他风行一时的佛教信仰相激荡,为各宗各派所接受,在理论支撑、体系建构、功能拓展、信众普及等方面超越所有神灵信仰,成为一种学理丰富、体系博大、功能多样、根基牢靠的信仰体系,将它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奠定了后世观音信仰进一步演变与拓展的经典依据、理论支撑和信众基础。
宋元之际,观音形象突然从原来的男性菩萨形象转变为世俗气息极浓的女子形象,在妙善公主和马郎妇故事的激发下,得力于民间的强劲推动和艺术家的灵活创造,女子观音的形象迅速普及,观音由此成为中国最流行的女神。这一形象转变既体现了中国人的勇气和魄力,也表达了中国人对观音慈悲精神的理解和需求,并由此上接西王母传说,下启无生老母信仰,各种各样的娘娘与老母乃至妈祖与神化的村姑纷纷涌现,推动形成蔚为壮观的女性神信仰潮流。从此,观音菩萨以亲切祥和、温馨柔美的形象及无尽的悲悯与无限的力量,深入民间社会及亿万民众的心灵深处,尽显其大众化、生活化与通俗化的气质,彻底改组了中国宗教神灵体系的基本格局和精神情趣。
明清之际,以观音为主尊的佛教道场大规模增加,以观音、圆通、大悲等内涵指向为限定,以寺、山、庵、台、洞、坪、庙为空间标识的观音道场,在各种灵验故事的渲染下成为中国佛教领域数量最大也最有影响的一种神圣空间。由此进一步发展,得益于浙东陆海地理位置、周边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早期已有的观音信仰传承,加之与经典所记观音道场的颇多一致,普陀山在成千上万的观音道场中异军突起,逐渐成为所有观音道场的第一代表,独占观音菩萨显灵说法之地的神圣角色,形成一山独大、万山呼应的神圣空间格局,以及“信观音,朝普陀”的全新观音信仰形态,并与五台山、峨眉山及随后跟进的九华山一起,组成四大菩萨、四大名山的信仰体系,支撑起明清以来汉传佛教最流行的一种神圣空间架构,成为菩萨信仰中国化的一种全新形态。
以上四种变迁,在时间上先后推进,在内涵上依次拓展,在形态上相继演化,成为中国宗教史上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其中任何一种历史变迁都携带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交织着中印、三教、圣凡、雅俗、政教以及人文与自然、理论与实践、现实与理想等多重关系,不但与中国佛教其他文化元素深度融合,成为中国佛教历史变迁的缩影,而且与中国宗教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密切呼应,成为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
可惜的是,学术界对信仰型佛教研究一直比较忽视。在以上四种观音信仰变迁的研究方面,普陀山作为观音道场,其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以及由此所交织的各种复杂关系,学术界的研究就更为薄弱了。特别是迄今未见通史之著述,也鲜见有系统的断代史之研究,正是在这一学术视野下,我认为《普陀山佛教史》堪称填补空白的学术创新之作。本书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广泛搜集普陀山佛教史的相关资料,将普陀山佛教发展放在中国佛教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梳理出不同朝代普陀山佛教发展史的基本脉络和基本特点。这不但是神圣空间视野下的观音道场通史,也是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观音道场的断代史。作为神圣空间的观音道场通史,《普陀山佛教史》以普陀山这一具体地理单元为观察对象,以观音信仰第一圣地的形成为思考焦点,以渊源和流变为核心线索,以佛教文化、地理空间以及政治经济等多重复杂因素为问题解读的历史素材,全面分析了文化地理意义下的中国观音信仰第一中心的形成。作为宋元明清时期的观音信仰断代史,《普陀山佛教史》力图再现那个特别时期中观音信仰的重大变化,借助神圣空间这一视角关联其他所有的历史元素,为我们呈现了那个特别时期的观音信仰状态。这一研究既有助于我们理解观音信仰的纵向发展轨迹,更有利于我们解读中国化观音信仰神圣空间的演变与定型及其在佛教信仰中的重要地位,真是可喜可贺!
整体来看,本书有以下四大创新:第一,研究角度的创新。已有成果虽有分门别类之细腻,但无溯源逐流之系统,作为学术界第一部普陀山佛教史,本书系统梳理普陀山佛教的演变历史,具体内容包括佛教传入普陀山的考证、宋代普陀山佛教史、元代普陀山佛教史、明代普陀山佛教史、清代普陀山佛教史和民国普陀山佛教史等,完整勾勒出了普陀山佛教的历史图景。第二,研究体系的创新。已有的普陀山佛教史研究成果缺乏体系性,因而很难从中看到普陀山佛教发展的整体轮廓。本书的研究涵盖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普陀山佛教之发展,侧重其在不同历史时期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阶层以及交通等方面的关系,涉及宗派发展、高僧贡献、宗风阐扬、山志编撰、神圣空间建构、朝山信仰的发展等多方面的内容,形成新颖而完整的普陀山历史诠释系统,蕴含着很多深刻的理论与思想。第三,研究方法的创新。已有的研究方法虽然运用了宗教学、文献学等研究方法,但是在历史学方法的运用方面仍欠深入。本书以历史学研究方法为基础,结合历代山志和古籍文献进行佛教史研究,同时借鉴宗教学、地理学、民俗学等方法,不同问题,不同进路,共同服务于总体进程的探索和把握。第四,学术观点的创新。在以上创新的基础上,本书在很多具体问题的研究方面都得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结论,实现了学术研究的不断超越,同时因为很多问题是本书第一次涉及,所以,也常能发前人之未发,努力拓展普陀山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当然,本书的价值还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观察。本书是对闻名世界的佛教圣地的历史研究,梳理了中国汉地信众最多的佛教圣地的形成演变史,破解了世界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世界宗教圣地研究提供了来自佛教历史的参照;同时,本书也是对浙东某一具体地域佛教的历史研究,为地方佛教研究提供了新的样本。本书是对印度佛教在华传播与拓展的历史研究,让我们看到印度佛教持续影响中国佛教的历史余晖;本书也是对佛教在唐以后持续中国化的探讨,证明佛教中国化是不同时代各有亮点的历史过程。本书既是对一种佛教神圣空间的历史研究,让我们在经典、名号、造像、咒语等神圣象征之外看到了道场的神圣象征意义;本书也是对一种菩萨信仰形态的历史研究,为我们勾勒出中国观音圣地信仰的形成和基本格局。本书挖掘的问题形形色色,不同问题之间彼此关联,形成绵绵密密的问题链条,在问题的不断破解当中揭示出丰富的历史内涵,相信有心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自会产生很多触动。我虽然没有仔细读完全部的书稿,但随着本书的脉络,品味很多观点,也引发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由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我在这里仅就普陀山如何成为《华严经》所说观音道场这一问题再谈一些自己的感想。
其实,对于一个宗教学者来说,只要愿意静下心来思考普陀山这一文化现象,尤其是对照人类宗教史上有关神圣空间的历史个案与学界的相关理论,并结合中国山水文化的背后思想与情趣,特别是五岳崇拜和洞天福地信仰,你便会发出由衷的感叹,普陀山不仅仅是一个闻名天下的旅游胜地,也不仅仅是一座简单的佛教名山,而是文化意义极强的神圣空间,在其形成、延续和发展变化的历程中,充盈着丰富的历史内涵,暗藏着诸多重大的文化密码,既点缀着有关地理、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民俗等领域的无数元素,也交织着理论与实践、人文与自然、宗教与政治、精英与民众、高雅与通俗、信仰与生活等多重复杂的关系,透露出中国佛教神圣空间的内在轨迹和特性,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将神圣意义的菩萨信仰与自然意义的地理空间,特别是“山”这种地理单元结合在一起,并借助菩萨的神圣性而在空间上进行象征性表达,不断建构地理空间的神圣意义,使自然的山变成文化意义的名山,再从文化意义的名山上升为宗教意义的圣山,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圣山信仰,这是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文化现象。在印度,婆罗门教特别是后来转型而成的印度教有神山信仰。佛教在释迦牟尼涅槃后逐渐兴起圣地信仰,尽管释迦佛与灵鹫山有一定关联,迦叶、龙树等圣者与鸡足山、吉祥山等也有关系,佛教教义中也有须弥山的蓝图,佛教故事中也有雪山等山的影子。但在各处说法场景的经典建构之外,在信仰实践中将实际存在的山作为崇拜对象,将朝山作为修行方式的宗教文化现象并未出现。即使后来在中国极负盛名的灵山,也是因为禅宗建构传法谱系的原因而得到中国人的格外关注。此后民间出现的远朝灵山的向往,更多是受中国佛教圣山信仰影响而出现的一种情感,但同时受到禅宗的批评,这已远非印度灵山原本的精神了。总之,古代印度应该没有佛教的圣山信仰,至少在密教出现以前。至于密教时期的圣山,可能更多的价值在于通过山来烘托菩萨的神圣,而不像中国是通过菩萨的神圣来建构山的神圣,使菩萨崇拜拓展甚至转化为山的崇拜。当然,中国佛教的这种转化是在中国山岳信仰传统的深刻影响下发生的。中国的山神祭祀源远流长,封禅思想经过一段酝酿之后,终于在秦始皇时代与泰山建立起直接的联系,而汉代以后兴起的五岳信仰更成为一种完整的山岳信仰体系,加之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假托自然以表达某种人文情怀的传统,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天地山川与花鸟虫鱼都被赋予某种人文含义。受此影响,道家也出现了洞天福地的神圣空间,道教名山不断增多,儒道名山体系支撑下的中国宗教文化便具有了浓厚的圣山崇拜特色。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唐以前的中国佛教顽强坚守源于印度的传统,并未出现佛教的圣山信仰。
但是,佛教的地理空间概念早在释迦牟尼时代就已经是佛教的一个重要文化元素。三界六道、大千世界、须弥山以及后来相继出现的净土信仰,都是佛教特有的地理单元,与佛陀直接相关的诸多地点,更成为佛教最早的神圣空间,在阿育王时期掀起了巡礼朝拜的热潮。在唐以前的中国,前往印度朝拜圣地已经是中国佛教的重要信仰,并出现了《佛国记》《释迦谱》以及唐初的《大唐西域记》《释迦方志》等佛教方志类作品,体现了中国人对西天佛教圣地的重视。而对中国本土来说,随着鸠摩罗什、慧远等大师级人物的出现,他们所在的寺院也在信众心目中具有了崇高的意义。但真正实现突破的,还是《华严经》汉译本出现之后。最先依据《华严经》建立的中国佛教神圣空间是五台山,从东晋翻译六十卷《华严经》到唐代华严宗的创立,经历了近三百年的时间,终于完成将经中所说“清凉山”指向五台山的中国化诠释与中国化实践确认,五台山遂成为文殊菩萨的道场获得中国人的信仰。同时因为《华严经》中文殊与普贤两大菩萨不可分解的呼应关系,在澄观等人的努力下,普贤菩萨的道场被安立在峨眉山,并在随后的时间里逐渐获得世人的认同,两大菩萨与两大名山的格局在中唐基本形成。在此后不久,发生了日本僧人慧锷从五台山请走观音像并最终供奉在今天普陀山的事件,或许还有某印度僧人在此见到观音显相的事情发生,可是在那时此地并未被认作《华严经》中所说的观音道场。也就是说,今天的普陀山其实存在着两个不同性质的历史转型:其一是从道教的洞天之中脱颖而出,成为万千观音道场之一;其二是从一般观音道场上升为《华严经》所说的观音驻地。前者叫梅岑山,后者叫补怛洛迦山,也就是今天简称的普陀山。
我和会闲法师联合指导的研究生慧观法师的硕士毕业论文研究的便是普陀山开山问题。她选择的是狭义的普陀山开山,即最初如何形成观音道场的问题。当初我曾经给她建议,所谓初期的开山,应该包括五个“形成”:第一,信仰对象的形成:观音主尊供奉的形成与最终确立,包括观音像的出现及被安置与供奉的情况、观音显灵事迹的出现和显灵信仰的传播、各种观音灵验与感应故事的出现等;第二,信仰群体的形成:僧众因为观音信仰的集体性驻锡及僧团组织体系与制度的形成,还有在家信众的出现及其作为一个信仰群体的形成;第三,信仰场所的形成:以观音信仰为核心的道场建设及道场架构的形成,包括最早供奉观音的场所,以供奉观音和修行观音法门为目的的场所建设的不断推进,以殿堂为主并包括各个神圣地点与神圣物或象征物的逐渐形成及其所展现的神圣空间体系的形成;第四,信仰仪轨的形成:以观音信仰为主的宗教仪轨与实践体系的开展,包括寺院各种观音修法,如唱赞、称名、礼拜、供养、庄严、诵经、节日、庙会、吃斋等各种与观音信仰直接相关的礼仪习俗等的形成;第五,信仰认同的形成: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认同,包括官方、士人、民众等不同领域对此地作为观音道场的认可。当然,就初期开山问题的研究来说,这些问题也不见得都能梳理清楚。而究其性质来说,这一研究还只是梅岑山时代的观音道场形成史,而非对接《华严经》及其他经典后的观音圣地形成史,更非作为四大名山之一的菩萨道场体系成型史。
从梅岑山到普陀山,本质上是对接《华严经》及其他几部记载观音宫殿所在地的大乘经典的过程。学术界一般认为《华严经》形成于西域,其核心地点在今天的和田。这部在印度本土之外形成的经典对中国人热衷的文殊和观音两大菩萨的道场有了空间位置的指定,并经过中国人的诠释,指向了中国本土之内。这种现象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在印度佛教史尤其是密教之前的印度佛教史上,并未出现佛教的圣山崇拜,可以说《华严经》开创了佛教圣山崇拜的端倪,为中国佛教的圣山崇拜提供了经典依据,并最终发展成远超《华严经》本意的菩萨圣地崇拜现象。相比较来说,文殊道场五台山仅仅是从经典中所说的“东北方”的清凉山转换为地点确凿的五台山,而观音道场则要完成从印度东南海滨到中国东南海滨的空间转移,所涉及的问题,远比其他佛教名山更加复杂。
《华严经》所说的观音道场就是善财拜见观音的那个“南方有山”。晋译《华严》讲到善财于南方拜见观音的那座山叫光明山,这座山在南方何处,则不得而知。玄奘西天取经时,到了南印度的秣罗矩咤国,据他说:“国南滨海有秣剌耶山。……秣剌耶山东有布呾洛迦山。山径危险,岩谷欹倾。山顶有池,其水澄镜,流出大河,周流绕山二十匝入南海。池侧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往来游舍。其有愿见菩萨者,不顾身命,厉水登山,忘其艰险,能达之者盖亦寡矣。而山下居人祈心请见,或作自在天形,或为涂灰外道,慰喻其人,果遂其愿。从此山东北海畔,有城,是往南海僧伽罗国路。闻诸土俗曰:从此入海东南可三千余里,至僧伽罗国(唐言执师子,非印度之境)。”这座山是否《华严经》所说的光明山?玄奘并未明说,我们猜测,如果玄奘从当地人那里听说此山就是善财童子参见观音菩萨的地方的话,玄奘肯定应该有所说明。玄奘未做说明,可见在玄奘看来,他不知道也不认为此山就是《华严经》所说的观音道场。从玄奘的记载来看,与此前传入中国的《华严经》上所说观音道场有所不同,除了名称有别外,晋译《华严》的观音道场并未明说是在海上,也没有确指印度本土的南方,可是玄奘所记载的此山的地理位置非常具体,尤其是位于海滨,要上山还需要涉水。同时玄奘还记载了与晋译《华严》不同的信仰风俗,就是信众不顾身命,忘其艰险,厉水登山,愿见菩萨显化,或者在山下“祈心请见”,观音就会化现为“自在天”或“外道”来满足信众的心愿,这已经有了明显的圣山元素和朝山信仰迹象。
玄奘于显庆四年(659)在大慈恩寺弘法院翻译的《不空罥索神咒心经》中对此观音道场的景象有详细描述:“一时薄伽梵在布怛洛迦山观自在宫殿,其中多有宝娑罗树、耽摩罗树、瞻博迦树、阿输迦树、极解脱树,复有无量诸杂宝树,周匝庄严,香花软草,处处皆有。复有无量宝泉池沼,八功德水弥满其中,众花映饰,甚可爱乐。复有无边异类禽兽,形容殊妙,皆具慈心,出种种声,恒如作乐。与大苾刍众八千人俱,九十九俱胝那庾多百千菩萨摩诃萨,无量百千净居天众,自在天众,大自在天众,大梵天王及余天众无量百千,前后围绕听佛说法。”这种景象倒是与晋译《华严》有很多相似之处:“处处皆有流泉浴池,林木郁茂,地草柔软。结跏趺坐金刚宝座,无量菩萨恭敬围绕,而为演说大慈悲经,普摄众生。”这种相似,很容易让人们将二者联系在一起。此后几乎所有译经家,如义净、菩提流志、般若、不空等,凡是涉及观音道场者,均为补怛洛迦山,虽然在个别用字方面时有差异。与此同时,自玄奘之后,观音道场为补怛洛迦山便成为中国佛教界的共识。
三十多年后,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实叉难陀开始在洛阳大遍空寺译《八十华严》,圣历二年(699)于佛授记寺译完。实叉难陀将晋译《华严》所说的善财童子参拜观音的光明山与玄奘记载的这个观音道场完全对等起来:“善男子!于此南方有山,名补怛洛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汝诣彼问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即说颂言:海上有山多圣贤,众宝所成极清净。华果树林皆遍满,泉流池沼悉具足。勇猛丈夫观自在,为利众生住此山。汝应往问诸功德,彼当示汝大方便。”不但名称从“光明山”改为玄奘记载的补怛洛迦山,而且位置也明确为玄奘描述的“海上”。此后的《四十华严》也是如此。
虽然《八十华严》将经中所说的观音道场与玄奘所记及其他诸经所说的观音道场画上了等号,但这个名叫补怛洛迦山的观音道场却依然远在印度的南海边。到了五百多年后的南宋末年,定都临安的宋政权对附近名山有高度关注,加之文化中心的辐射作用,梅岑山开始被指为补怛洛迦山,如志磐的《佛祖统纪》中说:“补陀山在大海中,去鄞城东南水道六百里。《大悲经》所谓补陀落迦山观世音宫殿,山有潮音洞,洞前石桥,瞻礼者或见大士善财净瓶频伽。”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也详细记载“补陀落迦山,自明州定海县招宝山,泛海东南”。当然,在唐宋之际,此山上的“宝陀”“补陀”“普陀”等名称与佛经中的“补怛”“布呾”也有彼此混同的足够机会。即使如此,元代盛熙明依然对此心生疑虑:“然世无知者,始自唐朝梵僧来睹神变,而补陀洛迦山之名遂传焉。盘礴于东越之境,窅芒乎巨浸之中。石洞嵌岩,林峦清邃,有道者居之,而阿兰若兆兴焉。自非好奇探幽,乘桴泛槎者,罕能至也。”他还曾描述观音道场的神奇景象,并因此认为“以是考之,则决非凡境,岂造次所能至哉,似匪此地比拟也”。可见,盛熙明曾经以“世无知者”来评论将补怛洛迦山“迁移”浙东海上的说法。可是,后来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后至四明,屡有邀余同游补陀山者,心窃疑之,不果往也。一夕,忽梦有人谓曰:‘经不云乎:菩萨善应诸方所,盖众生信心之所向,即菩萨应身之所在,犹掘井见泉,然泉无不在,况此洞神变自在,灵迹夙著,非可以凡情度量也。’既觉而叹曰:‘嗟夫!诸佛住处,名常寂光,遍周沙界,本绝思议,何往而非菩萨之境界哉?断无疑矣!’”盛熙明的这种思想转换,可能代表了宋元之际中国人认识和接受普陀山的普遍心理。若深究其背景因素的话,可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印佛教关系的突变。从两汉之际到两宋之际,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印度佛教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输入。西行求法与东来弘法彼此激荡,在译经、解经、讲经的同时,学派形成,宗派创立,制度完善,信仰普及,思想渗透,实践展开,印度佛教的活水源头在支撑和激发中国佛教发展的同时,也对中国佛教发展方向起着引领和框范的作用。12 世纪开始,印度佛教急速衰落,到13 世纪初,终于彻底衰亡。这个时候正是中国的两宋时代。经此打击,持续千年的印度佛教入华史终于画上了句号。印度佛教向中国输入的终结以及中印佛教交往的停滞和由此开始的中国佛教的独立发展趋势,不但使印度佛教的所有圣地与华夏大地实现了阻隔,从而失去了在中国佛教信仰者心目中的圣地意义,而且导致印度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急遽减弱,为中国佛教的自由创造和自成体系提供了不受约束的广阔空间,极大地加速了中国化佛教信仰形态和实践体系的形成,特别是中国化佛教神圣空间体系的形成。
第二,中国佛教发展轨迹的转型。与中印佛教关系突变这一背景相关,中国佛教在唐宋之际发生重大转型,从原来的以经典义理为中心转变为以信仰修行为中心,在理论情趣不断减弱的背景下,宗派会通沉淀为禅净呼应的核心框架,而佛教的实践却迈开了更加自由的步伐,在终极超越的诉求依然保持的背景下,应对现实生活问题的信仰显示出持久不衰的生命力,佛教不断向简易化、通俗化、生活化、民众化方向发展,以菩萨信仰为标志的佛教信仰大兴并渗透到底层社会,对民众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化的菩萨信仰体系开始了全新的构建过程,在布袋弥勒和女性观音相继出现的同时,神圣空间的建构也迈开了勇敢的步伐,最终以四大名山的格局呈现出来。
第三,观音道场的激增。随着中国佛教发展的转型,隋唐时期已经出现的观音随处显化信仰,在宋元以后的中国大地上形成“千处祈求千处应”的增长态势,大量观音道场涌现出来,它们一般都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将观音菩萨作为信仰的主尊,表现为观音殿、大悲殿或圆通殿等;二是据文献记载或传说,曾发生过观音菩萨显灵等感应事迹;三是驻锡此地的僧众和常在此活动的信众主修观音法门;四是形成以观音菩萨为中心的修行仪轨甚至节日或庙会等;五是作为观音道场在一定范围内获得信众的认可。在以信仰对象为主尊的佛教寺院中,除了具有教主身份和普遍象征意义的释迦牟尼佛之外,主供观音的道场成为数量最大的一类。这种历史现象为普陀山上升为观音第一道场提供了信仰的基础。
第四,山林佛教传统的增强。佛教自古以来的出世精神与静修传统使山成为佛教格外喜爱的修行之地,从而形成浓厚的山林气息。印度早期佛教的阿兰若就多有位于山林之中者,部派佛教时期很多教派的高僧就生活于山间,大乘佛教中观学派创始人龙树曾长期驻锡吉祥山、黑峰山等地,瑜伽行派创始人无著早期也曾经在山中修行十多年。到了 7 世纪以后的密教时期,山的神圣性日益明显。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并未见有圣山崇拜的痕迹,但魏晋时期佛教受崇尚自然的玄学的影响以及战乱时代安稳静修的需要,出现一股隐居山林的清风,庐山、终南山、会稽山、蒋山等都与佛教结下很深的缘分,从几部僧传也可以看出,僧人居山成为普遍现象。山野林间与城乡红尘之间在地理特性上的鲜明差异进一步烘托了佛教的批判精神和解脱追求,中国佛教的山林静修情怀与都市弘法精神并行不悖,由此发展便出现了“自古名山僧占多”的繁荣景象。当然,魏晋隋唐时代的山林佛教基本保持着对社会的观察、批判和超越,而宋元以后的山林佛教在理论情趣淡化、信仰精神日浓的背景下,逐渐陷入一种逃避社会的自我封闭系统中,批判和引领社会的能力日益减弱。在专制统治日益强化、儒家文化笼罩一切的背景下,被不断挤压的佛教更加崇尚山林,并继续承担创伤抚慰、苦难应对及终极超越等方面的宗教功能。总体上看,山林佛教的文化内涵是多元的,特别是其中的神韵与神秘的力量和神圣的境界更容易产生某种想象中的关联,从而就更容易赋予这种特别地理空间以神圣的意义,并向圣山信仰方向发展。
第五,中国山岳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山岳崇拜,特别是儒道两家的圣山文化,对佛教名山现象的出现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源于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赋予山川林泽、风雨雷电、鸟兽木石、日月星辰等自然物以神圣的意义,并通过祭祀等神秘方式与这些崇拜对象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以解释和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神山、圣山、灵山、仙山等山岳信仰便在这种宗教传统中逐渐成长起来,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的昆仑山与蓬莱仙山及西汉时代体系化的五岳信仰,中国的山岳信仰扮演了中国宗教历史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特别是从秦始皇开始的封禅以及汉魏兴盛起来的洞天福地,将儒家的国家治理和道家的身体修炼与山岳崇拜密切结合在一起,将中国的山岳崇拜推向宗教范畴之外,也为山岳崇拜开拓了更加广阔的社会生存空间。走过隋唐五代,到了宋元时期,儒道和民间的山岳崇拜已经蔚为壮观,佛教再也无法抵挡中国传统山岳信仰的魅力,作为道场所在地的山开始了整体性神圣空间的建构,特别是通过菩萨显灵说法等神迹的塑造,山被赋予神圣性内涵,开始转为崇拜的对象。普陀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打开了通向圣山的门径。
第六,唐宋历史的变迁,特别是南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学术界有所谓唐宋变革论,认为唐宋之际在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民族关系、文化特性、民众精神等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中出现的平民崛起、地方发展、俗文化兴盛、商业发达、经济中心南移等历史现象,对普陀山的兴起有重要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安境保民,稳定一方,经济发展,文化昌盛。尤为重要者,是吴越国历代统治者重视佛教文化,故浙江一带迎来了佛教发展的又一高峰期。到了南宋时期,杭州作为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对周边产生强劲的辐射作用,佛教文化在周边地区获得迅猛发展。普陀山的真正崛起,可能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关于这些变迁对普陀山圣地形成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尚不到位,本书中有所涉及,难能可贵。
第七,宁波及其周边地区在太平洋西岸海上交通中拥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不但带来繁荣的商业,而且促进了佛教文化交往的发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地处宁波外围舟山群岛的普陀山脱颖而出。与唐宋历史变迁密切相关,在发达的海上贸易激发下,作为海上交通要道的舟山一带不但是南北航线的必经之地,而且成为东北亚海上贸易路线和东南亚海上贸易路线的交汇处,来自北方渤海沿岸,南方福建、广东,以及海外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各地的船舶在此往来交流。《佛祖统纪》记载普陀山潮音洞观音显化后接着对其海上交通位置有所说明:“去洞六七里,有大兰若,是为海东诸国朝觐,商贾往来,致敬投诚,莫不获济。”《(宝庆)四明志》记载慧锷带观音像上船时是同商人一起的:“以之登舟,而像重不可举,率同行贾客尽力舁之,乃克胜。”《大明一统志》的“补陀落迦山”条中说,“往时高丽、日本、新罗诸国皆由此取道,以候风信”。从这些宋代的资料来看,普陀山一带的确是商道所经之地。这一方面形成繁荣的商业贸易,另一方面也成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化往来的交汇之地,促进了海上佛教文化交流的发展,对普陀山圣地角色的形成起到一定的激发作用。
第八,与印度补怛洛迦山地理的高度一致。首先,普陀山和印度的补怛洛迦山同位于大陆东南沿海。其次,海陆形势相似,上补怛洛迦山和上普陀山都需要渡海涉水。再次,两座山的地形地貌也比较接近,树木葱郁,泉流潺潺,池塘盈水,花果丰盛,绿草柔美,山石嶙峋,鸟鸣和悦。以上这些相同之处,为梅岑山转变为补怛洛迦山提供了方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相同之处则在于,它们皆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前文已经说过中国普陀山的海上交通位置,我们再看印度观音道场的海上交通枢纽地位。印度东南沿海的补怛洛迦山,往南航行即是斯里兰卡,往东航行,穿越印度洋,并经马六甲海峡,可抵印尼、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再经南海北上,可通往我国和日本、新罗等东亚国家。根据玄奘旅印期间所作的考察,“从此山东北海畔,有城,是往南海僧伽罗国路。闻诸土俗曰:从此入海,东南可三千余里,至僧伽罗国”。其中的僧伽罗国,即是今天的斯里兰卡,这是一条什么样的海上通道呢?《贤愚经》说:“又闻海中,多诸剧难,黑风罗刹,水浪回波,摩竭大鱼,水色之山。如斯众难,安全者少,百伴共往,时有一还。”《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说:“乘大舶船,入于大海,向东南隅,诣其宝所。时遇北风,漂堕南海,猛风迅疾,昼夜不停。”《佛本行集经》说:“于大海内,有诸恐怖。所谓海潮,或时黑风,水流漩洄,低弥罗鱼蛟龙等怖,诸罗刹女,如是等师。”我们再看看观音菩萨的救难功能,就明白观音道场为什么会在海上贸易的交通要道之地了。《普门品》中说:“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车磲马瑙珊瑚虎珀真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赍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这里所说的观音救难类型都与商贸尤其是海上商贸有关。可见,观音道场在海上贸易交通要道处出现是有原因的。在印度东南沿海的补怛洛迦山如此,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普陀山也是如此。
除了上述八个方面的背景因素外,普陀山成为佛经上所说的观音圣地的历史转换可能还与当地民众的响应、士大夫的宣传、僧人们的支持、统治者的认可等因素密切相关。在普陀山圣山化的发展过程中,交织着太多的文化关系和历史元素,形成多方互动发展轨迹。总体上看,观音道场从印度东南沿海到中国东南沿海的空间转移,渊源于晚唐,开始于宋代,明确于元代,并在明代获得全社会的公认。印度观音信仰向中国的传播,在完成经典翻译、教义诠释、实践开展等环节之后,终于完成观音第一圣地的空间转移,连同宋元时期的观音女性化,代表着印度观音信仰中国化的最终完成。
会闲法师器宇清肃,心境澄明,自幼在普陀山出家,对观音圣地怀有深切的感情。经历多年的普陀山修行后,他又远赴斯里兰卡凯兰尼亚大学求学,终获博士学位。2018年5月,我们荣幸地邀请会闲法师担任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兼职教授,参与相关研究和研究生指导工作。法师慈悲应允,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和支持。前些年,他还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顺利出站后,继续作为常务副院长,主持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的全盘工作。在会闲法师的努力下,普陀山学院业已形成完备的教育体系,特别是在专业创设方面大胆探索,不断实践,尤其值得赞叹的是在全国首先提出并设立了观音学专业。所谓观音学就是研究以观音信仰为核心的佛教文化现象的学问。从纵向来看,观音学主要梳理和研究观音信仰在古代印度的产生、发展、演变、流传以及印度观音信仰向外输出,特别是向中国输出的过程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与演变的历史进程及其所涉及的中印、政教、僧俗、夷夏等诸多关系的演变;从横向来看,观音学主要研究和把握观音信仰所蕴含的各种理论,尤其是哲学理论、宗教理论以及其他各种思想学说,探索佛教的“神学”体系与特征,研究以观音为题材或以观音信仰为核心的各种文学与艺术作品及其特征与诸多文化关系,梳理观音信仰中所包含的伦理、民俗、养生等文化现象及其在民众生活中的表现与深刻影响。
无论纵向,还是横向,都交织着很多重要的问题,其中观音道场与神圣空间便是中国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与会闲法师分别在普陀山学院和西北大学鼓励研究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有这方面选题的学位论文相继完成。2018年5月16日,会闲法师率领“普陀山佛教协会朝圣参学团”25位法师参加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举办的“观音信仰与神圣空间的建构—从终南山到普陀山”的学术座谈会,并在发言中从终南山与普陀山各自的历史演变、文化内涵与文化地位的角度,论述了两座文化名山之间的遥相呼应与内在联系,同时就观音信仰在这种文化关系当中的支撑与导领作用以及两座圣山在今天文化建设当中的现实价值进行了说明,并对两座文化名山的研究者与守护者提出了殷切的希望,言语当中饱含着对两座文化名山的深切感情。我在发言中讲述了终南山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文化地位,尤其是终南山观音文化的内涵及其在整个中国观音信仰发展史当中的重要作用,并从观音文化的角度论述了终南山与普陀山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也涉及佛教菩萨信仰与中国山岳文化之间的关系。普陀山和终南山,在观音信仰的神圣空间建构过程中极具代表性,如果说终南山在历史上导引了观音信仰神圣空间建构的发端,对观音信仰的发展走向产生重要影响,那么普陀山则成就了观音信仰神圣空间的最终建构,在唐以后观音信仰体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终南山与普陀山交相辉映,见证了中国观音道场信仰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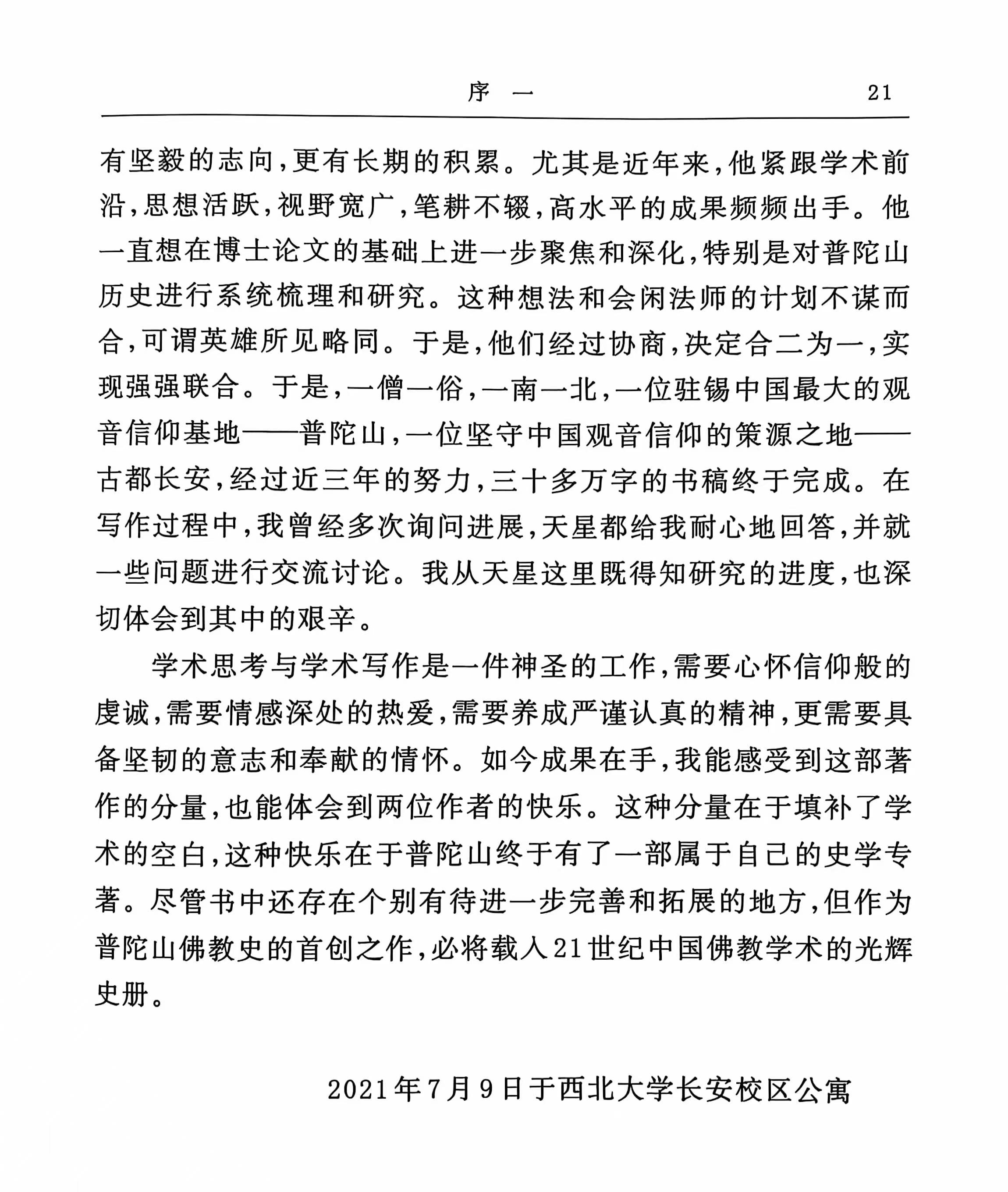
特别令我感怀的是,本人非常荣幸地得到会闲法师的信任和嘱托,自2012年开始担任普陀山学院观音学专业研究生导师,协助会闲法师培养观音学方面的人才,截至目前共招收研究生5届,业已毕业3届共9位,在读的还有两届共5位。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知识、学术、思想、智慧四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从知识的学习到学术的研究,再到思想的提升,最后的考验则是智慧的体悟与运用。对于人生来说,年轻时一直在学习,更多是知识的积累。到了研究生阶段,从知识的学习逐渐转变为学术的研究。但学术毕竟为“术”,有思想才应该是学者的更高追求。思想建立在认识社会和体认生命的基础上,思想的灵魂在于一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对于从事佛教研究的人来说,智慧代表的却是一种更加高远澄澈的境界,修学智慧便成为生命品质的终极支撑。在我看来,会闲法师就是一位懂学术、有思想,同时也洋溢着佛教智慧的人。还在我刚刚认识他的时候,他便提起撰写普陀山佛教史的想法,并多次与我交流。在我看来,他的构思是细密的,他的策划是有眼光的,这不仅体现了对普陀山的深厚情感,更证明了他在学术思想方面的稳健成熟。
本书的另一位作者是景天星博士。他来自山西,大学毕业后专职从事五台山文化研究,后又进一步深造,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得硕士学位。前些年,他又举家来到西安,入西北大学跟我攻读博士学位。鉴于他曾经从事五台山文殊道场的研究,我那时刚好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宋元明清时期中国汉地观音信仰研究”,我便建议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确定为观音道场信仰研究,以普陀山为核心。景天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建议,勇敢地踏入了这一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领域,并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一部让各位评委大为赞赏的博士学位论文。天星品性善良敦厚,待人热情大方,处事严谨认真,在学术方面也颇有慧根,并有坚毅的志向,更有长期的积累。尤其是近年来,他紧跟学术前沿,思想活跃,视野宽广,笔耕不辍,高水平的成果频频出手。他一直想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和深化,特别是对普陀山历史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这种想法和会闲法师的计划不谋而合,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于是,他们经过协商,决定合二为一,实现强强联合。于是,一僧一俗,一南一北,一位驻锡中国最大的观音信仰基地——普陀山,一位坚守中国观音信仰的策源之地——古都长安,经过近三年的努力,三十多万字的书稿终于完成。在写作过程中,我曾经多次询问进展,天星都给我耐心地回答,并就一些问题进行交流讨论。我从天星这里既得知研究的进度,也深切体会到其中的艰辛。
学术思考与学术写作是一件神圣的工作,需要心怀信仰般的虔诚,需要情感深处的热爱,需要养成严谨认真的精神,更需要具备坚韧的意志和奉献的情怀。如今成果在手,我能感受到这部著作的分量,也能体会到两位作者的快乐。这种分量在于填补了学术的空白,这种快乐在于普陀山终于有了一部属于自己的史学专著。尽管书中还存在个别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拓展的地方,但作为普陀山佛教史的首创之作,必将载入21世纪中国佛教学术的光辉史册。
2021年7月9日于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公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