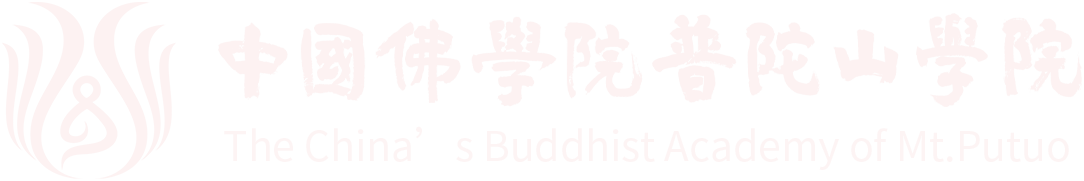《普陀山诗词鉴赏》九十一
2024-12-23
补陀山(四首)
陆光祖
天抱琉璃宮,鳌柱不见底。谁骑香象来,明月弄空水。(一)
山椒石壁寒,沙岸水痕泐。涛声日夜喧,禅心自空寂。(二)
白马驮经来,乃在大海外。谁知震旦中,有此无色界。(三)
宝殿低秋浪,疏钟入夜风。身心无处著,始悟本来空。(四)
【背景】
此诗在明·周应宾撰《重修普陀山志》卷五(诗题相同)及民国·王亨彦撰《普陀洛迦新志》卷二(诗题为)嘉兴陆光祖:补陀山诗》)以及《普陀洛迦山志》卷八、《普陀山诗词全集》“明部分”中均有收录。

作为明晚期朝廷清流,陆光祖为政胸怀忠直,力持清议,凡相处或闻其人者,“翕然归之”,但也因此招致不少人的忌恨与排击,曾被迫多次请退家居。在家居期间,陆光祖则潜心于佛法,发愿护教,并尝发起募捐、组织刊刻《五灯会元》,并合力重兴明州育王寺塔殿,还与冯开元等居士共同发起募刻小本藏经。晚年时,与紫柏真可大师相从交游,即便卧病在床也口诵真言,手执印相,始终不懈。因此陆光祖无论对佛教的贡献还是个人的行持,在当时居家学佛人士中皆堪为翘楚。
《普陀山诗词全集》共收入陆光祖的四首诗,分别为《洛迦山望海二首》《宝陀寺漫兴》《赠普陀僧》及《补陀山(四首)》。从《补陀山》四首组诗来看,对普陀山可谓全方位的描绘,从中也可以展现出诗人对于佛教的情怀以及个人修持的状况。
第一首诗的前两句从总体上鸟瞰了普陀山的特征,即普陀山乃是观音菩萨住止的“琉璃宫”,既然是“天抱琉璃宫”,漂浮在大海之中,那就必须有一个“鳌柱”在中间支撑,而这根“鳌柱”却深不见底。“琉璃宫”既已存在,那么就需要主人的到来,故“谁骑香象来”,似乎给我留下一个悬念。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明月弄空水”,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主人为谁,但从明月与水的关系之中,我们自然想到了千江印水,看到了菩萨的感应道交。第二首诗谈到了普陀山上的一些具象景物,“山椒山壁寒”说明此时已入深秋,“沙岸水痕泐”,沙滩边的海水波纹荡漾,与山上的石壁相互映衬。而大海一日两度潮,并不会因为白昼黑夜的轮换而有所止歇,潮来潮去,日夜喧闹不休。这种看似变动不居的现象背后却大有禅机可觅,即潮来观“有”,潮去观“空”,一来一去,累劫如是,故而形成规律,从中可得潮涛之声其性本为“空寂”,这与“禅心”恰为暗合。而观音大士的证悟历程,恰与海潮音密切相关,即通过海潮音的听闻进而反闻自性,最终获得解脱。
第三首诗谈到了佛教传入中国乃源自于“白马驮经”,此记载耳熟能详。但长期以来,佛教基本上都是在关中及中原及黄河以北一带流传,故而远离于“大海”之外。但是当陆光祖来到大海之中的普陀山之后,竟见到此处的佛教氛围比之海内,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诗人惊叹“谁知震旦中,有此无色界”。一旦修到了四无色定,那么基本上可以脱离对物欲的贪求,甚至连色身都不复存在,全部聚焦于精神享受之中。从这两句中,足见佛国僧民精神境界之高。
最后一首是陆光祖暂居于普陀山的身心感受,他每天出入于寺院殿宇之中,听闻着寺院的若有若无的钟声,观睹着一日两度如期而来的海潮,沐浴在清新舒缓的夜风之中。经过一段时间佛国大士恩光的照沐,此时他似乎洗尽了尘世的铅华,身心逐步达到“无处著”的地步——他甚至获得了某种契悟,“始悟本来空”,只要身心无有牵挂,不执着,万念放下,那么无论什么样的名闻利养,都无法羁绊自己,成为自己的枷锁。至此,陆光祖悟出了“万法本空”的般若境界,实属难得希有!
无论是为人还是为官乃至学佛,陆光祖在历史上均有良好的口碑。在为人处世方面,《罪惟录》说“掌铨不图报复,世以为难,乃益用推引提护,岂非有得于好恶恶知美之旨者乎?”在《本朝分省人物考》也称其“私居无戏言,无遽色,平生怜才仕事,任嫌任怨,凛然有古大师风节焉!”纵观其诗,作为晚明文人,在世风日颓之下,竟能自言“自心无处著,始悟本来空”,即便是究经皓首的缁门大德,恐怕也不过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