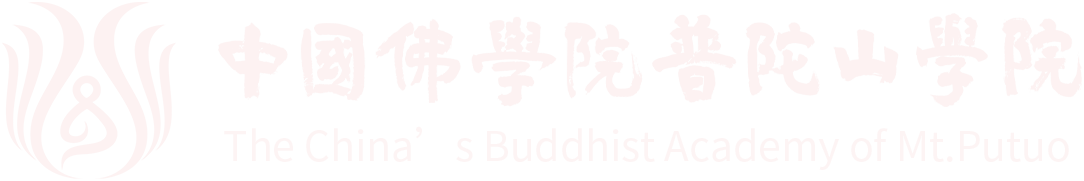《普陀山诗词鉴赏》九十八
2025-02-10
题补陀
郑有学
相传大士此中住,共说真如今有无。
隐见月光呈瑞相,氤氲花气学香炉。
迷津可渡舟樯满,圣水无边岛屿孤。
我若有观应自在,何须锦字问麻姑。
【背景】
此诗初收于明·周应宾缉撰《重修普陀山志》卷五,《普陀洛迦山志》及《普陀山诗词大全》均有收录,诗题相同。

【鉴赏】
从明代中晚期诗人的艺术风格来看,除了以儒学作为立身处世之本之外,似乎皆有佛、道兼学兼修的倾向,这从本诗辑所选赏的明代诗文中就不难看出,例如在歌咏佛教名山普陀山时,往往将之与梅福、葛洪、蓬莱之类的仙岛相联系,而本诗中的“麻姑”,则是典型的道家仙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诗人对于道教人物也深有涉猎。
本诗从宏观层面叙述补陀洛迦。前两句属于叙述史实,即“相传大士此中住”,虽然佛经中有观音菩萨常住于补陀洛迦的记载,但是那是《华严经》中所叙述的神圣境界,与现实中的南印度海岛以及中国的南海普陀也未必完全等同;此虽不能等同于菩萨的根本道场,但作为菩萨的应化之地,则是无懈可击。而既然作为菩萨的应化之地,菩萨在山中所说之法乃是“真如”,“真如”乃是众生的本来面目,也就是法性或虚空佛性。其中的“共说”,说明不止大士一人,而是所有诸佛菩萨皆说“真如”法门。从这个意义上说,“真如”实际上就是解脱生死的法门,而悟入此法门,就要解决现象世界和思维世界的“有”“无”问题。“有”与“无”是一种对立,执“有”或执“无”都是一个极端,只有突破了“有”与“无”的对立,才有可能悟得“真如”,这是诗人从另外一个角度向我们表达了他对观音法门的认识与理解。
在颔联的两句中,似乎将普陀的现实情景与佛理相融合。诗人选取了两个角度,一是“隐见月光”,二是“氤氲花气”。“隐见月光”是说夜晚阴晴不定,云彩也是忽左忽右,故而所观的乃是时隐时现的月光,而这也正是大士音容的写照;“氤氲花气”谈到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花香之气,然而这种香气从何而来,又让人看不见摸不着。但无论是“隐见月光”还是“氤氲花气”,可是说都是佛国特有的佛教氛围:看似平常的月光以及司空见惯的花香,在大士的加持之下,却呈现出“瑞相”以及像香炉里飘出的一缕袅袅青烟。
在颈联的两句诗中,诗人又将视角放到了普陀山周边的茫茫大海之上。大海虽辽阔无边,然而在诗人看来,只要皈依大士并修习大士法门,就一定能够达到彼岸。在这里,诗人怀着无比乐观的心情写道“迷津可渡舟樯满”,在补陀四周的海岸边上全部是可以载人渡海的“舟樯”,只要迷人愿意,就随时可以登上驶向对岸的舟筏;而补陀岛屿虽“孤”,而托起这座孤岛的乃是“圣水”,即便众生身陷海涛之中也不足为虑,因为圣水可以降福,可以驱邪驱魔,可以医治众生百病,所以无需为自己的生死而担惊受怕。从这个意义上说,补陀乃是一座圣山,四周大海乃是圣水,这一切都是大士慈悲加持的结果。
在尾联之中,诗人将眼光又从具象返回到抽象的思惟之中,他觉得生死与解脱大事,每个人自己最有选择权和发言权,如果能像观音大士那样“有观”,即透过现象观照本质,那么最终必然获得突破,从而得大自在,畅游于生死海中而来去自如。倘若如此,我们又何必花大量的时间去撰写“锦字”(即道家所撰写的青词或青辞),去向麻姑仙人请教求仙之道呢?诗人言下之意是,在补陀大士足下用心参究就绰绰有余,而完全不必费时费力去访道修仙。而这两句诗,也是诗人扬佛而抑道的最直接表达。倘若在崇道日盛的嘉靖一朝,撰写这两句诗,其实是要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的,足见诗人勇气可嘉、诗品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