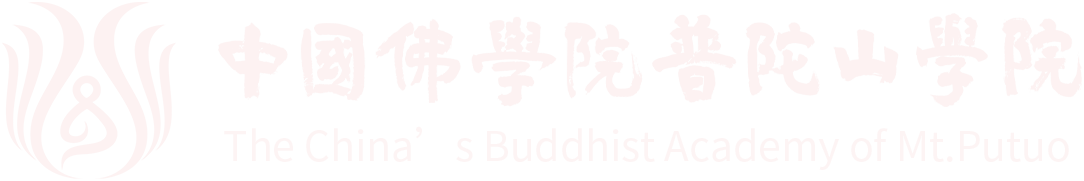《普陀山诗词鉴赏》九十九
2025-02-17
登补陀
刘尚志
欲问如来何处寻,宝轮空里海涛深。
朝看绝岛开龙象,夜听寒潮落梵音。
万顷风云浮碧玉,九天日月布黄金。
阆州恍在藤萝外,梦入西方不住心。
【背景】
此诗最收入于明·周应宾的《重修普陀山志》卷五中,民国王亨彦《普陀洛迦新志》卷二、王连胜主编的《普陀洛迦山志》卷八以及《普陀山诗词全集》中均有收录,诗题相同,作者署为“刘尚志(皖人,海道副使)”。

【鉴赏】
作为明代皖籍优秀代表人物之一,刘尚志家族一家三代人中出一位状元、三位进士、一位贡生、一位武举人、二位解元,可谓典型的书香门第,诗书人家。刘尚志与普陀山结缘,当在明万历十五年(1587)正月,其时刘尚志笔浙江按察司副使,实际就是分管海道的副使。十七年(1589),刘尚志受邀为补陀山作《补陀山志序》,而这个山志,究竟是屠隆、侯继高等所编的山志,还是周应宾所修的山志,从史料来看,似乎属于前者,因《序》有这样一段文字:“万历己丑仲春日,巡视海道、浙江按察司副使、前刑科右给事中、皖城刘尚志记”。其中“万历己丑”(1589)与屠隆所作序时间相同,该序中有“开府侯大将军乃谋之兵使者刘公、郡大夫龙公,纂修《补陀志》”。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时,此时刘尚志升任浙江右布政使,从二品,在任期间挑选良半,苦练精兵,扩修战舰,以防倭寇。而在任职浙江期间,还与莲池大师结缘,刘为大师作《净慈讲圆觉经雪中送别皖城刘景孟方伯》诗,称大师“薇垣瑞彩动南屏,佛国重开了义经……行看霖雨慰苍生”之句。
在诗文方面,刘尚志同样具备了不俗的文采,仅就《补陀山志序》一文来看,全序通篇近四百字,字句明畅清朗,文辞精深玄妙,极具华彩而不失简约,斐然成章,读来琅琅上口,颇得格律之韵。文虽简短,却准确地描述了补陀山的地理风貌、人文特点及刘尚志对于佛教有着独到见解,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由于刘尚志传世的诗文并不多,《登补陀》一诗可视为其难得一见的七律诗。从史料上看,刘尚志登岛的原因,除了普陀山乃佛教圣地之外,明代普陀山也是重要的海防前线,距离普济寺南方不远的山顶之上尚存有明代抗倭时的炮台以及防空洞,这些皆可作为佐证,因此刘尚志登岛的目的无非就两个,一个是视察海防情况,二是顺道礼佛。诗的前两句也直抒此行的目的,即“欲问如来何处寻,宝轮宝里海涛深”,其言下之意是自己受到宝轮的指引而来拜礼观音如来。“宝轮”一词来自于转轮圣王所拥有的七宝之一“金轮宝”,其长年累月地在空中旋转,并发出耀眼的光芒。当宝轮开始向哪个方向前进,国王便带领四种兵跟随宝轮的方向前进,只要宝轮所到之处,所有国家臣民均会夹道欢迎,虔诚臣服,此即所谓的“以法治化”,也就是宝轮所代表的是人间的至理,也是天下人所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诗人正是在宝轮的指引下前来补陀礼佛,尽管需要跋山涉海,但是他坚信宝轮所在之处就一定寓示着祥和与安宁。
从诗的三、四两句来看,刘尚志在普陀山当留有几日光景。清晨,“朝看绝岛开龙象”;夜晚,“夜听寒潮落梵音”。所谓“绝岛”,是从补陀的地理位置而言,虽显得孤绝,然山中法门龙象无处不在——退一步说,从普陀山地形上看酷似龙首,而龙头朝北(梵音洞加上合兴村方向形似龙头张开巨嘴)。所谓“寒潮”,间接点明时间,此时天气尚寒,这与“万历己丑仲春日”是一致的,普陀山具备倒春寒气候特征,故用“寒潮”十分贴切。然而“寒潮”并不“寒”,却成了清净灭烦恼焰的 “梵音”,夜中卧听寒潮之音如同梵音奏响,反衬出诗人此时心境格外地平静。
从白天来看,“万顷风云浮碧玉”,从远处眺望,整个山体就好像万倾波涛中浮起的一块碧玉;而金沙、百步沙、千步沙弯曲连绵,达成了“金镶玉”的审美效果,既高雅(玉)又不失富贵(金)。在诗人看来,碧玉乃“万顷风云”所浮起,黄金乃“九天日月”所布下。诗人在游历之时,显然被眼前的美景所陶醉,一时间似乎出现了某种幻觉:“阆州恍在藤萝外,梦入西方不住心。”阆州即阆苑,传说中是西王母的所居之地;此时诗人甚至觉得这种仙境就在不远处的“藤萝”之外,向前轻迈几脚便可信步而入;既便是梦中到了西方,也不会舍不得离开,因为眼前就是仙境,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能住于此山之中,夫复何求呢?最后两句诗,将诗人对普陀山的赞美之情推向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