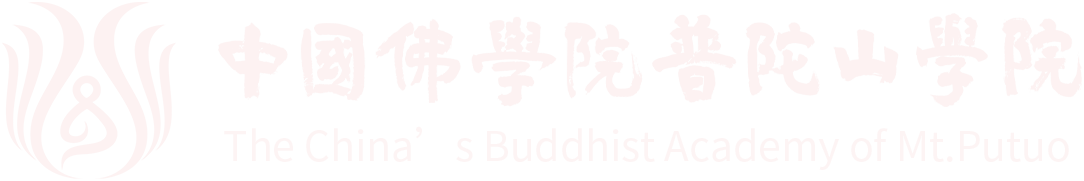《普陀山诗词鉴赏》一百
2025-02-24
游补陀山
冯梦祯
西教东流到补陀,金莲花发映娑罗。
星河历历粘青汉,岛屿累累浸白波。
龙献宝珠归象罔,僧留香饭与鼋鼍。
我来欲发如来藏,老傍寒松学鸟窠。
【背景】
此诗最收入于明·周应宾的《重修普陀山志》卷五中,民国王亨彦《普陀洛迦新志》卷二、王连胜主编的《普陀洛迦山志》卷八以及《普陀山诗词全集》中均有收录,诗题相同,但作者署名有所差异,周《志》作“浙江嘉兴冯梦祯(祭酒)”,而王《志》作“嘉兴冯梦正”。

【鉴赏】
作为晚明文士,冯梦祯与佛教因缘深厚,其与紫柏真可大师的法谊更是为后人所称道。史载万历二十八年(1600),紫柏北上欲搭救南康太守吴宝秀,冯梦祯与汤显祖等人都极力规劝,紫柏虽未接受善意,然对冯梦祯等江南挚友的友切与爱护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紫柏大师于1603年在北京坐化狱中后,冯梦祯异常悲愤,抑郁久之,仅两年之后,冯即忧愤而逝。另外,冯梦祯与屠隆虽皆有佛情,但屠隆偏重于道,而冯却一门事佛,并对净土行门情有独钟。据称冯时常劝说屠弃道而归佛,并且去信批评道家之学,如“足下比道业何似玄门中人,自圣贤至盗贼,种种俱有。圣贤不常得,盗贼比比,且其所兵,人人异端,汪洋汗漫,莫知适从。”从这里可以看出,冯梦祯的护教情怀十分炽烈,这在明代官宦人士中是十分鲜见的。
冯梦祯是何时朝礼普陀山,史志中所言不详,只是说“尝游普陀,作《游补陀》诗”。从诗中来看,既从宏观层面谈到了佛教流布中土的过程,并且也结合普陀山情景谈到了自己对于教理的理解。首句是“西教东流到补陀”,“西教”指佛教,事实上佛教在普陀山流布的时间一般定为唐咸通或大中年间,此时距离佛教传入中国已有八百年之久,可以说总体流布较为缓慢。然而后来者居上,自从观音道场形成后,使金莲遍山绽放,其兴盛甚至超过了印度本土的娑罗花。“星汉历历粘青汉”是指天象奇特,所谓佛选名山,名山的成就绝非朝夕可成,必须具备大功德大因缘;而“岛屿累累浸白波”指的是东海海域岛屿众多,但令人惊奇的是,观音大士在众 多岛屿中唯独选中了补怛洛迦作为自己的应化道场,这其中必有感应道交的成分。而这种感应的成分,集中体现为两个:一是“龙献宝珠”,其事迹取材于《法华经》卷四“提婆达多品”,龙女有一宝珠,价值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供佛,佛即纳受,于是龙女谓智积菩萨与尊者舍利弗言:“我献宝珠,世尊纳受,是事疾不?”答曰:“甚疾。”龙女言:“以汝神力观我成佛,复速于此。”(《大正藏》第九册,第35页下),“归象罔”一语则取材于《庄子·天地》,“象罔”为人名,助黄帝而觅得宝珠,喻宝珠留山,自然会熠熠生辉。而下句的“僧留香饭与鼋鼍”则不知出自何典,存疑待考。此二句从总体上说是指普陀山之所以形成佛山效应,其中有着甚深的因缘。
最后两句是诗人由衷的愿望:“如来藏”乃众生本具的清净自性,但是众生犹如垢衣缠身,却从不识自己心中的这颗摩尼宝珠。唯有当下静滤,深入思惟观察,方可逐步悟透如来藏心,从而转识成智、转迷成悟。诗人认为,身处佛国氛围之中,自己对于世间的各种名闻产生了厌倦,甚至萌生了剃发出家修道,像鸟窠禅师那样栖身于老松树之上,从此不问任何人间是非功过。然而诗人又深知,身为世俗中人,又岂是一个“舍”字所能了结?末句中的一个“老”字,道出了诗人的无奈与纠结:有太多的事和太多的人需要自己去亲自打理,看来只有等到自己彻底地“老”了,退休了,再来做个专精修道的苦行僧吧!而这种心态也契合了世间大多数人的想法,他们时常说:等我退休了,我就到寺院里来修行吧!然而直到临终的那一刻,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愿望都无法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剃除须发染衣出家为僧,实在是不容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