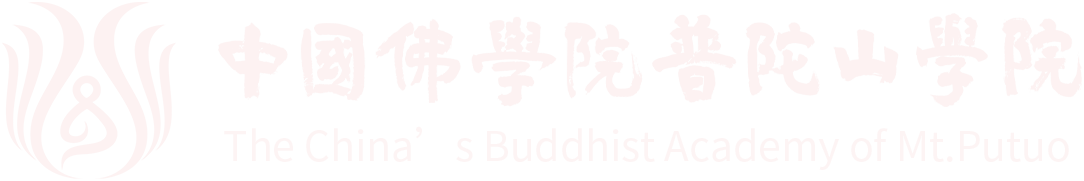《普陀山诗词鉴赏》一零一
2025-03-03
题洛迦
龙德孚
望来鳌柱淼无涯,海上孤悬小白华。
说法台高开宝藏,潮音洞逈涌金沙。
扶桑夜沸三更日,祇树光生五色霞。
我亦有冠惭未挂,梅岑何处觅丹砂?
【背景】
此诗最收入于明·周应宾的《重修普陀山志》卷五中,民国王亨彦《普陀洛迦新志》卷二、王连胜主编的《普陀洛迦山志》卷八以及《普陀山诗词全集》中均有收录。关于作者籍贯与官职,各山志大多署为“湖南武陵人,宁波府同知”。关于此诗的创作时间,《普陀洛迦山志》认为是万历十八年(1590),是年身为宁波海防同知的龙德孚赴普陀调处寺僧相讼事件,赋《题洛迦山》诗一首,归印《法华经》百部送寺。

【鉴赏】
明代的沈一贯在《印法华经歌序》中提到龙德孚早年奉道,甚至还有出家为道士的打算。在任职宁波府同知期间,曾亲赴普陀山处理僧讼事件。“一日,过普陀勘事,而疑僧众之不斋也”,据说这种怀疑受到了夜梦神人的警告。至于这段时间寺僧相讼事件,《山志》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至少可以说明普陀山在晚明时期僧团内部也并非和合无诤,而是间有摩擦,否则也不可能上升到请求官府出面裁决的地步。从《歌序》中可知,龙德孚与法雨寺(海潮庵)的创立者大智禅师法缘深厚。另,万历十七年(1589)时任宁波总兵的侯继高便与府丞龙德孚议修《普陀山志》,并请屠隆主持编纂。但即便是虔诚奉佛,龙德孚也没有放弃对道教的信仰,如万历二十年(1592)在龙德孚的努力下,清道观得以恢复,在《重修清道观碑记》中称“东岳行宫由郡丞龙德孚主持重修”,这再一次印证了“佛道兼修”在晚明文士中是一种普遍现象。
龙德孚赴山原本是为了处理僧人之间的相讼事件(也可能是寺院之间的一些纠纷),因此起初对寺僧有着一定的轻慢;但当他踏入普陀山之后,思想观念上发生了一些改变。从诗中可以看出,当时龙德孚参礼了西天(说法台)、潮音洞以及后山的海潮庵一带。从远处看,“望来鳌柱淼无涯”,茫茫大海浩瀚无边,而所有岛屿似乎是飘浮在大海之上一般。对于古人来说,这些岛屿之下都有一些“鳌柱”撑举,否则便会掉入海中。“海上孤悬小白华”,这样的诗句在古诗中十分常见。而颔句中提到了“说法台”,位于西天磐陀石东面不远处,传说观音菩萨曾在此说法。正因为菩萨在此说法,海中生灵都纷纷前来闻法,至天明时都不舍离去,结果造就了二龟闻法石以及五十三参等传说故事。在潮音洞旁,诗人看着深不见底的洞口,再看不远处的沙滩,此时随着海浪之声,诗人似乎听闻到了大士的说法之音。联系到龙德孚曾夜梦神人传佛旨,此时他对菩萨的感应事迹更加深信不已,故而在诗人看来,说法是一种“开宝藏”,而潮声则无疑是向众生输出珍贵的“金沙”。
诗人虽然以“说法台”和“潮音洞”作为普陀山的典型意象,但从普陀山的现留圣迹来说,这两处无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接下来的颈联二句则似乎从眼前景物走向了联想的空间,“扶桑夜沸三更日,祇树光生五色霞”,“扶桑”在“三更”里依然“夜沸”,似乎是指夜里海潮之音;“扶桑”“祇树”用在此处,当然是指佛国普陀,“光生五色霞”当指清晨,站在百步沙或千步沙边,旭日东升,五色霞光自然照射四方。潮鸣彻夜,昼日霞披,似乎隐喻着此处乃扶桑仙境,祇园再世。诗人此时的心情似乎开始释然:身处于佛光的沐浴之下,什么样的恩仇情怨不能放下?诗人甚至都开始感到惭愧:自己身在俗世有功名在身,很难做到抛弃一切“挂冠而去”,但是作为宁波府的同知,此时竟能心中有“惭”,说明思想境界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最末一句“梅岑何处觅丹砂”,此处指出普陀山古为仙岛今为佛山,即便是佛山,但仙迹依旧,于是诗人作出大胆的相像:料想汉代的梅福道人,一定还在山中的某处起炉炼就丹砂吧?诗人在结尾中提到了梅福与丹砂,料想也有其深意所在吧!
史载龙德孚“中岁好道,调息守中,晚节事佛”,这也大体符合过去文士的一贯风格:少年习儒,以安身立命,光宗耀祖;中年修道,以调养身体,延年益寿;晚年事佛,以一意西驰,植福后世。纵观明代文人诗文,大多四平八稳,中规中矩,见真性情者鲜(至清代也大致如是)。这说明诗文发展到明清时期,几无亮点可陈。从龙德浮的诗来看,也大体符合这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