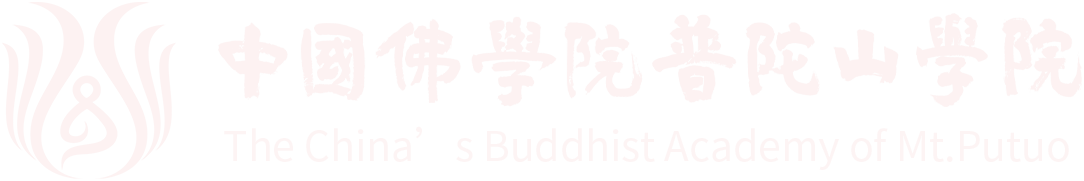《普陀山诗词鉴赏》一零三
2025-03-17
题补陀
李言恭
五岳三山总浪游,法门高敞海天秋。
窗前云气蛟龙起,槛外波光岛屿浮。
月映宝珠明上界,星随灯火散中流。
黄尘白发真无赖,彼岸慈航何处求。
【背景】
此诗在明·周应宾的《重修普陀山志》卷五、民国·王亨彦的《普陀洛迦新志》卷二、王连胜主编的《普陀洛迦山志》卷八以及《普陀山诗词全集》中均有收录。《普陀洛迦新志》诗题为“题补陀诗”。

【鉴赏】
从现有《山志》资料来看,也很难查到李言恭抵达普陀山参礼的记载。从常理上说,李言恭作为明代开国功臣李文忠的八世孙,世袭临淮侯。李文忠是明太祖的外甥,而李文忠在明立国后受封曹国公,其子李景隆在永乐二年被废爵位,一直到嘉靖十三年才加封李文忠的五世孙李沂为临淮侯,一直传到十一世孙李祖述。李言恭在从政从军路上并无大的建树,然其作为中军都督府的主政官员,其来到普陀山自然也是旌旗招展,鸣锣开道,然而史志中却对此事鲜有记载,故令人疑惑。
李言恭虽是行武出身,但其身上的文人气息很重,经常吟诵诗句;而且其对佛道皆很有兴致,这从其号“青莲居士”“秀岩道人”中就可以看得出来。“青莲居士”是李白的号,“秀岩”形容山中景致,从这里大致可见李言恭虽身披铠甲,但骨子里却是对文士充满了钦慕并刻意摹之。从本诗中来看,作为官宦子弟,李言恭自称是“五岳三山总浪游”倒并不为过,也就是说,五岳三山都浪游遍了,然而这些名山对他来说并没有感到特别之处,但是大海中的一处仙山却没有历览,让他心下难平。于是在秋天的一天,他来到了舟山普陀。而诗人之所以选择了海中普陀,乃是此处的“法门高敞”,即法门大开迎接四方朝圣者;“海天秋”既指出时节,也侧面映衬出诗人此时愉悦的心情。
从诗中可以看出,来到舟山(或普陀山)后,李言恭被安排在岛上的一幢寓所之中,此处濒临大海,所以朝夕时总可以看到海上云雾缭绕,恰似一条条巨大的白色蛟龙腾空而起,盘桓在海岛的四周;当云雾散云之时,诗人踱出寓室,凭栏眺望着远处的海岛和天空,“槛外波光岛屿浮”,海面上浮光跃金,远处的岛屿在波光之中上下浮动,好像漂在大海之中一样。
如果说颔联写的是昼日间的海景,而颈联则是描摹夜景。上句的“月映宝珠海上界”,如果将普陀山作为夜晚的一颗宝珠飘浮在黑沉沉的大海上,“星随灯火散中流”,天上有群星闪烁,海中及陆地上有零星的灯火流动。如果说“月映宝珠”是一种实写,那么诗人此时所站的角度,则似乎并非身处普陀山,而是站在大海对岸的沈家门渔港。如此一来,李言恭很可能没有亲赴普陀山,而是在对岸的沈家门留宿一夜后便匆匆离去。如此一来,最末两句就容易理解:军务在身的诗人虽然是“黄尘白发”,一路风尘仆仆前来参礼补陀,但多少有些“无赖”——此处的“无赖”,既可以理解为“无奈”,也可以理解为自己虽然“黄尘白发”,但仍然童心未泯;而“彼岸慈航何处求”中的“彼岸”也有二解,一是理解为对岸的佛国海岛,二是与生死相对的解脱境界。若是属于前解,那么似契合了此时诗人正身处沈家门而未临普陀山的推测。然无论如何,即便是像王勃那样遥钦大士,也算是了却了自己多年来的一桩心事——即便是未登佛国,然大士道场近在咫尺,从“彼岸”和“慈航”而言,可谓何处不彼岸、何处不慈航?如是想来,想必诗人心下释然,也不再为此而执著抱憾了。
从诗歌成就上看,李言恭虽出身行伍,然其诗词水平总体上居于中上等,无论是绝句还是律诗,大多对仗工整,且具有一定意境,如《晓渡》的“云与人争渡,春随客到家”、《汉江城楼》的“人家半渔者,簔笠挂秋风”以及《山居乐》的“夜静白云鹤睡,春深红树莺啼”,这些诗句皆有隐士之风,从中也可看出李言恭虽出身显赫,然其仍然怀着一颗出尘淡然之心。对于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附庸风雅,从明一代的执政理念中,我们似乎体悟出功臣后代们也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苦衷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