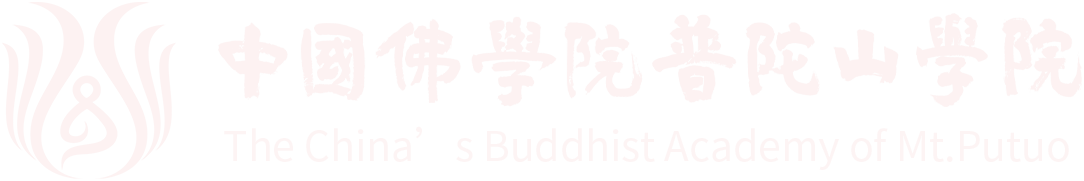《普陀山诗词鉴赏》一零六
2025-04-07
寄赠昱光禅师
李橒
遥从皈大士,白业佐名山。
根利超三昧,心空悟八还。
林深依月静,海旷度云闲。
自恨尘劳缚,无缘观法王。
【背景】
本诗最早选自明·周应宾的《重修普陀山志》卷六,诗题相同。《普陀洛迦山志》卷八与《普陀山诗词全集》均有收录。

【鉴赏】
《重修普陀山志》及《普陀山诗词全集》共收入李橒的三首诗,分别为《题洛迦》、《白华庵方丈落成赠朗彻上人》及《寄赠昱光禅师》,并题“李橒,鄞人,司马”,而民国王亨彦的《普陀洛迦新志》则只收入《题洛迦》一首诗。不过在《居士传》与《吴都法乘》中,皆明确提到了李橒,称“玉受与前巡抚李橒巡按史永安等分城守”,这是指李橒署理巡抚贵州时率众抗击叛乱的事迹。
从李橒现存的三首与普陀山有关的诗词来看,其不仅朝礼过普陀山,而且与白华庵的昱光大师、朗彻大师都是非常要好的文友(并且与昱光大师皆是宁波同乡),昱光与朗彻是师徒关系,当时昱光大师似乎已退居,由其徒朗彻继为白华庵住持。从李橒的两首诗中,可以看出诗人对两位高僧赞不绝口,称“说法人共集,施食鸟众鸣”,说明当时白华庵文人香客荟萃,佛事昌隆,其在普陀山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在明中晚期,来山文人墨客赞颂昱光师徒的诗句较多,如丁继嗣的“证果白华岭,超然出世先”、“花发传灯后,龙皈说法前”(《游白华庵为昱光上人题》),其中说谈到了大师的修行境界以及说法时的摄受力;杨大名的“茗椀说元龙注沫,竹林分紫佛传宗”以及“双跏未许惊朝坼,百铄无嫌速暮钟”(《寄酬白华庵昱光上人与其徒朗彻》),谈到了师徒二人的禅定功夫以及在茶道方面的造诣。尤其在茶道方面,《阳羡砂壶图考·雅流》篇中就记录了如曜昱光对于茶壶的酷爱,“昱光、朗彻师徒,蓄金石、书画、文玩、茶具皆富”。另外,师徒二人不仅爱壶藏壶,还定制了为数不少的紫砂壶,该书中就记载有一柄壶“盖内铭‘白华庵’阳文小篆方印,底刻楷书铭四行,铭曰:‘清人树、涤心泉、茶三昧、赵州禅。佛生日、丙申年(万历二十四年,1596),释如曜铭,赠天然’”。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大师在行持之时,很好地将“赵州禅”与“茶三昧”二者融汇一体,从而获得茶禅三昧。
这是首五言律诗,整体韵律对仗平仄四平八稳,坦率地说,诗中自然也没有什么特别耀眼的诗句。“遥从皈大士”是说自己长久以来早已皈依了大士,或者说从前世就种下了善根;“白业佐名山”中的“白业”,可以理解为那些德行清净的居士,或者延伸到龙天护法,“佐”就是辅佐、佑护。而“根利超三昧,心空悟八还”以及“林深依月静,海旷度云闲”四句,集中描写了昱光长老所具备高妙的德业与道业。“根利”缘于上句的“遥从皈大士”,彼此互为因果;而“根利”与“超三昧”、“心空”与“悟八还”(“八还”是泛指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又形成了因果关系,即“根利”能够“超三昧”,“心空”才能“悟八还”。“三昧”是禅定,是自我的寂静与澄清;“八还”是对自然界生灭现象的深刻认识,二者共同构成法界。而“林深依月静,海旷度云闲”则是昱光禅师修行状态及生活态度的总体展现:夜晚在林中参禅打坐,白天则像海潮与游云一般来去无踪,从而彰显出昱光大师行持的精进与秉性的从容。
诗人在上面四句集中盛赞了昱光大师后,最后两句写到了自身的状态,即“自恨尘劳缚,无缘观法王”。身为俗人,且沉浮于宦海,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岂能说放下就放下的呢?此二句也道出诗人的无奈,而世人只看到文人的才气与为官的荣耀,却无从知晓他们的真实想法。由此二句使人自然联想起欧阳修《醉翁亭记》的那句话:“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其实欧阳修的内心并不快乐,否则又怎会“颓然乎其间”呢?欧阳修的“乐”,只能以“酒”来激发;而李橒的这份“恨”,却在“茶”“禅”之间渐渐得以消融,由“恨”转“喜”,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作者:界定